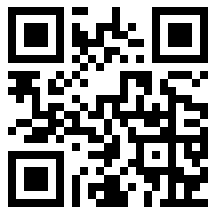總經理會議”、交叉持股、綜合商社……日本財團以其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手段展現了其強大的綜合作戰實力
二戰結束后,日本經濟全面崩潰。從戰后初期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日本企業的競爭力遠遠比不上美國和歐洲的企業。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不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世界100家大企業中,日本只有4-5家;在包括美國企業的世界100家大企業中,日本還榜上無名。
為了提高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50年代,大企業之間合并、協作以及產業再組織論,成了當時日本政策思想的主流。日本政府認為,小企業體制是本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差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因此,迅速改變這種現狀,擴大企業規模,扶植主導產業,就成了日本政府經濟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為了培育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日本政府和經濟團體聯合會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3年,日本政府修改了《禁止壟斷法》,放寬了持有競爭關系的公司的股份及兼職的限制,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舊財閥在美軍占領時期被分割出去的企業又重聚起來了。同時,戰后的一些“新財閥”也相互結合,形成芙蓉、第一勸銀及三和三大新型財團企業集團,這就是日本著名的六大財團型企業集團。這些集團最顯著的特點便是以金融機構為中心,集團內各企業環形持股,即銀行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交叉持股。
此外,日本政府還鼓勵大壟斷企業相互之間通過相互持股、系列貸款、人事互派等紐帶結成企業集團,以增強團體對外競爭能力。通過放寬對企業相互持股、系列貸款、人事互派等方面的限制,直接促進了日本企業集團的形成和發展,出現了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第一勸銀等“六大企業集團”和日立、豐田、新日鐵等若干“獨立系企業集團”。這些大集團橫跨各產業,構成日本經濟的基礎,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并對國民經濟有著重要影響。
網狀生存 三菱、三井、住友、富士(芙蓉)、三和、第一勸銀是日本著名的“六大巨頭”,前三者是直接繼承二戰前財閥譜系的集團,大約在50年代前后形成;后三者是在戰后日本經濟發展過程中,以主辦銀行為中心于六七十年代形成。
戰后六大財團和戰前金字塔型的財閥在組織結構上迥然不同,財團內各個成員企業,在經營決策方面保持著各自的獨立性。在財團企業中,有一個連接各個成員企業的直接紐帶經理會。這個名為“總經理會議”的會議是各個成員企業總經理定期聚會交換信息(情報)和交誼的場所,同時“總經理會議”也是各公司領導統一決策和協調財團戰略發展的“總參謀部”。日本財團正是以“總經理會議”和互相持股為基礎建立起了企業間的聯合體,財團的向心力也隨著成員企業間合作和資源整合而得到不斷加強。
以“總經理會議”為紐帶的戰后日本財團,表面看起來松散,而實際上確實聯系緊密。在最高領導人的任用上就可見一斑,被稱為東芝“重建之王”的前任社長土光敏夫曾經是三井財團另一企業石川島播磨重工的社長。在東芝經營出現極大問題的時候,時任東芝董事長石板泰三(后出任日本經團聯主席)直接任命土光敏夫為東芝社長(總經理)。這種高級經理人在財團內部流動,在當時和現在都是十分普遍的,這種現象比較類似于中國國有大型企業間的高層變動(特別是電信行業)。
財團的另一核心部分就是綜合商社,綜合商社是財團的情報機構,同時又是拓展海外市場的先鋒,它在財團內部有巨大的協調能力。日本企業最初進入一個地區和國家的時候,他們一定會第一時間找到本財團綜合商社在當地的分支機構,尋求他們的協助。各財團為了發展和壯大自己的綜合商社,都不遺余力地提供各種支持。1995年,世界500強的前4名都是日本綜合商社,前10名中有6家是日本綜合商社。
以三井財團為例,50年代初,由三井銀行發起成立了月曜會(總經理會議),接著以促進三井物產公司的合并為目的而成立了總經理一級的五日會,1960年改名為二木會,逐漸成為三井財團的統籌領導機構。50年代末,原三井財閥直系、旁系公司以企業集團的新形式集結而恢復成為大財團。三井財團的經理會成員公司及其子公司和關聯公司共達150多家。而三井物產則在1995年世界500強排名第二,并且連續5年以上進入世界500強前三名。
主辦銀行和綜合商社在財團內進行資金融通及集團內交易,同時也組織成員企業參與巨型項目、共同投資和拓展海外市場等,這些集團進攻的案例在中國市場也屢見不鮮。但是現在的日本財團不存在上下支配關系,因此我們把財團稱為“橫向集團企業群”。成員企業間互相持股,謀求股東的長期穩定,是財團的一個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縱向集團企業”也是日本大型企業所必備的一個特征,這類集團企業是一個在母公司一元化、垂直領導下活動的有機的事業集合體。日本的幾乎所有大型企業作為母公司在其系統中擁有大量的關系公司。所謂關系公司是指包括母公司持股超過50%的子公司和持股超過20%以上的相關公司,在中國就有大量這種日本企業的關系公司。母公司不僅對關系公司投資,而且還向其派遣高級管理人員直接參與經營。關系公司的數量按集團(group)不同有所區別,通常在100-200家左右,當然也存在像東芝、豐田等那樣擁有1000家以上關系公司的集團企業。
這些關系公司在母公司業務多元化發展和垂直性整合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在這一過程中,既有通過資本參與,將現存的交易對象作為關系公司納入集團旗下的,也有將母公司內部組織(部門)作為獨立公司分離出去的情況。另外,隨著日本經濟國際化而出現大量海外子公司,已經占據了關系公司的相當部分。
日本企業這種“做大做強”和中國企業的“做大做亡”形成了鮮明對比,其自身培養企業的方式與那種靠資本運營 發展企業有本質的區別。沒有強大的管理和技術基礎,通過資本運營 壯大企業,得到的企業成長是不穩定的,甚至會葬送企業。
不過,應該強調的是,這兩種集團并非各自完全不同的兩種形式。例如,三井物產是三井這一“集團企業群”(二木會)的重要成員企業,但同時又形成在其系統中擁有數百家關系公司的三井物產集團。事實上,日本企業的集團是由這兩個層次的重疊構成的。
日本的集團企業,通過母公司持股、派遣高層管理干部等手段開展經營活動。然而集團企業的經營活動范圍并不僅限于集團內部,許多制造業企業將集團外部的中小企業群作為長期、經常性交易的對象,即“外包公司”,實際上將它們納入自己業務經營的內部范圍。“外包公司”有的朝著水平方向延伸,如三菱公司擁有190家成員公司,年銷售額超過3000億美元;有的朝著垂直方向發展,像豐田汽車公司,擁有175個初級供應廠商和4000多個二級供應廠商。
此外,在主要的制造商(像松下公司)和全國幾千個零售商之間還存在著銷售聯盟。局外人要想打入系列內部,真是比登天還難。這樣一來就將大量的中小企業納入大企業的生產經營軌道,在互補、互利的基礎上,增強抵御外國資本和產品的能力。它與富有日本特色的法人交叉持股體制一起,形成保護國內產業和市場的復雜自我保護網。
“法人資本主義”與“民有國營”
日本企業的股份所有結構非常獨特,其集團企業股權結構和歐美企業完全不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前,日本集團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包括董事長(會長)、總經理(社長)在內的董事會由40人左右的董事組成,同時他們又是企業的實際經營者。
2000年以后,日本有些集團企業,如索尼等,都開始改變股權結構引入外部股東,但是根深蒂固的交叉持股和企業間長期積累的關系并沒有輕易改變。日本這種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方式和美國那種大眾持股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析的方式不一樣。日本公司的持股結構主要是由金融機構、事業法人、個人和外國投資者四類組成,其中一個特點是金融機構、事業法人、個人持股比例較高。例如,1992年,日本全部股票上市公司持股主體的持股比例為:金融機構持股為41.5%,事業法人持股為24.5%,個人持股為23.2%。這種相互持股的主要好處是有了共同利益的關系,企業間可以相互支持,互通情報,同心協作,共同發展。
{page}需要指出的是,公司董事會成員的持股比例非常低,雖然部分日本企業開始引入期權機制,但是大多數傳統的日本企業董事會成員的持股依然變化不大。1992年三井財團的東芝公司,董事會成員36人,持股合計51萬股,其比例僅僅為0.016%。當時被認為比例較高的松下電器,董事會成員為32人,持股合計1790萬股,比例為0.85%,這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在代表日本的這些巨型企業中,經營者幾乎并非具有實際意義的所有者。
日本巨型企業的主要股東幾乎為法人所有,因此這種資本主義被歐美國家稱為“法人資本主義”。日本政府和財團對經濟的影響和干預很大,而且企業管理者調動和任免一般都要服從財團和政府的計劃 ,各個法人股東的持股率并不足以進行單獨的支配企業,而且董事會大部分都是內部董事,公司的實際控制權就落入職業經理人手里了。
我們把這種公司治理稱為“民有國營”經濟。日本和韓國把那些本國的巨型企業稱為“社會型企業”、“國民企業”,這些企業雖然有特定的股東,但是普遍的觀念是這些象征國家的企業是全體國民所有的,并非個人財產。這些企業的興衰存亡直接影響到“國運”。
二戰后日本經濟急劇增長、企業規模日益擴大,股票所有廣泛分散,形成了從“按所有權支配”到“不按所有權支配”即“經營者支配”的結構。法人股東更多情況下與其說是為了“支配”本身,不如說是為了反映企業的關系程度,特別是穩定的交易關系。銀行和金融業為財團企業的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同時這些法人股東幾乎從來沒有干涉過持股企業的經營活動,甚至不要求過高的分紅,這些為日本的職業經理人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能力的舞臺。
走出“失去的十年”
日本以財團機制進行國家經濟管理是歷史(戰時)、地理(資源)、文化(儒學)和戰略(反殖民)等各種綜合因素的產物。
其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在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統治的世界中團結全民的力量,迅速獲得有效的競爭優勢,在全球范圍內爭奪原料、技術和市場。日本1955年加入關貿總協定前后采取的政策,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對抗外國列強經濟統治的意志和手段。正是這一時間開始,日本采取“穩定股東工作”的措施,重新組建主辦銀行和綜合商社為核心的、聚集大型企業形成的以相互持股和外部董事為特征的財團體系。與此同時,國家經濟命脈真正掌握在這些財團企業內部培養起來的、高度忠誠的、具有責任感的、實踐型的職業經理人(穿西裝的軍隊)。這種由財團機制建立起的日本模式,或由此形成的東亞模式成為發展中國家在短期內迅速躋身于經濟強國,并形成持續發展能力的成功典范。
在日本企業融合和形成新型財團時,有一個集金融、產業和商業的結合點——綜合商社。日本財團的本質就在于“財團”二字,財代表“金融”、團代表“商幫”。金融中的企業間相互持股被稱為日本財團的“艦隊護航體制”,而綜合商社則是現代商幫的體現形式。財團的存在在日本看來是歷史的選擇,是生存的選擇,也是日本經濟發展階段性的體現。
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和期間的亞洲金融危機,人們普遍認為是日本經濟體制的問題,但是這實際上僅僅是日本經濟的戰略調整和應對新經濟所做出的轉型。拉美國家經濟和東南亞國家經濟之所以受到跨國公司的操縱,最終引起大規模的金融危機,政府不得不聽命于外國勢力的計劃 ,關鍵在于其國家和政府為贏得一時的經濟增長而放棄了國家經濟主權,沒有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建立起自主的財團體系。
所謂財團體系,實際上就是將現代戰爭中以集團軍組織結構為基礎的多兵種合成作戰體系引入到了經濟活動中。一般人都感覺“戰略”這個詞通常是軍事領袖使用的術語。但是,在日本綜合商社的工作過程中,每當遇到投資項目時,頻繁使用的單詞不是“利潤”,而是“戰略”,還有一個通常使用的單詞就是“統合”。另外,我們通常所說的“項目”這個詞也幾乎都被日本人說成是“事業”。
事實上,日本現代企業制度來源于二戰時期的戰時統制經濟政策,保留了非常突出的軍事體制和計劃經濟的痕跡,成為日本戰后迅速崛起的重要法寶。研究日本經濟管理千萬不要只看到其著名制造業的企業管理模式,應該更多地同時關注日本財團內部的三股力量:綜合商社、主辦銀行、大型制造企業,它們之間是一個有機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整體。其中,綜合商社這種獨特的經濟組織在日本社會中扮演者極其重要的角色。
綜合商社是日本經濟的總參謀部,是日本國家經濟戰略的制定者,同時也對日本政治、外交和軍事等方面具有很強的政策影響力。日本政府對世界經濟事務的認識和研究幾乎完全依賴于財團的研究機構。例如:三井財團的“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和三菱財團的“三菱綜合研究所”。實際上,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研究和制定都是來自于對在世界范圍內收集的各種情報分析和研究。日本綜合商社在經濟情報方面有著無與倫比的巨大資源,這也決定了它在國家經濟決策中的重要地位。?中國目前的現狀有很多方面類似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1955年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1964年舉辦奧運會,整個五六十年日本的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高于10%。當時的日本制造業屬于產業鏈的低端,經濟的快速發展得益于低廉的人力成本和成功的對外貿易。日本企業以上述獨特的方式抓住機遇完成了資本和技術的快速積累其“貿易立國”政策帶有很強的重商主義色彩,使日本在短短二十年內就完成了追趕老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任務。因此,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的政策和發展歷程對我們認識當前經濟形勢和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諸多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