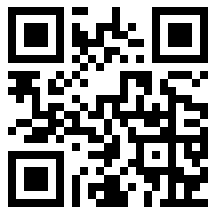美國電影《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就是一部很好地展現了領導者如何闡釋工作的意義,通過建立使命感推動團隊達成更高的目標的影片。這部戰俘逃亡電影中的巨制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為紀念二戰勝利二十周年而拍攝。影片一開始,是一群盟軍戰俘被德國人集中到一座新建的戰俘營中。這座戰俘營是專為關押空襲德國占領區的盟軍空軍而建,這批人以個人能力強、不安份而出名。為此,戰俘營采用了德軍所有能用上的安全手段,以防止戰俘逃跑。

果然,在新戰俘營開營的第一天,很多“不安份”的人就開始了種種嘗試:有人鉆入清運車中想混出去,有人在研究如何利用警衛瞭望視線的死角穿越鐵絲網,有人試圖混入外出伐木的蘇聯戰俘隊伍里……但這種種嘗試在反逃亡經驗同樣豐富的德軍看守面前無一奏效。其實,從戰俘營逃出去還只是開始,后面還要面對更大的麻煩:戰俘營外面情況不明,到處都是德國人,一旦被抓到,將受到令人生畏的非人折磨,關禁閉、毒打甚至是槍斃。因此,逃跑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嘗試的,更何況負責管理新營地的德軍上校馮•魯格采用了懷柔政策,給這些盟軍空軍戰俘提供盡可能好的“誘人”待遇,營內有運動場、圖書室、娛樂中心,甚至還提供園藝工具、種子等等,希望和他們達成一種相安無事的默契,靜待戰爭結束。
但是,一個關鍵人物來到,改變了這里的一切。這個關鍵人物就是英軍少校羅杰。羅杰是一名堅定的逃跑分子,簡直就是“屢敗屢戰”標準的逃跑版注釋,曾領導了多次逃跑行動。在羅杰的價值觀中,被俘的軍人仍是軍人,作為軍人就不能放棄戰斗,逃跑是被俘軍人的作戰方式。正是羅杰本人的價值導向,使得戰俘營的盟軍戰士對于“逃跑”有了全新的認識,逃跑并不是怕死的表現,逃跑也不再是放棄,而是另一種形式的戰斗。羅杰提出了一個極具震撼力的目標:“我們不是要跑出去兩個、三個,十幾個,我們要逃出去250人,散布到德國各個地方,制造混亂,讓數以千計的原本可以調往前線的德軍不得不留在這里當看守……”這樣一來,逃跑不再只是為個人奔向自由的零散的個人行動,而是戰俘們在另一個戰場以另一種形式發起的戰斗,“要戰斗就會有犧牲,但軍人不會因犧牲而畏懼戰斗”,也不應當因逃跑不成受到的折磨而擔憂,更不會為德軍的小恩小惠所羈絆。
“逃跑”的戰略意義被挖掘出來后,逃跑成為一場有組織的軍事行動,戰俘們建立了嚴密的組織體系,制訂了詳盡的實施方案,包括對德軍的監視系統、信號傳遞系統的破解,同時開挖三條地道,并分派有專長的人去負責,有人負責準備地圖、指南針、干糧和火車時刻表,有人負責制作假證件,還有人要準備逃跑出去后的衣服……這可是個極具號召力的行動,戰俘營中所有官兵的潛力被充分調動起來,大家為這個計劃而激動,被目標所激勵,連那些原本不主張逃跑的戰俘也被吸引加入到這個空前的計劃中來。
正是羅杰對于“逃跑”的意義的解釋,使得戰俘營中的盟軍官兵又有了存在的意義和行動的方向,從戰俘營中跑出去,從此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這也是《大逃亡》在眾多戰俘逃亡影片中有著獨特地位的原因。
經理人常常運用設立目標、制定計劃、監督跟進等方法來推動團隊及下屬行動,但如果僅僅這樣做常常成效不佳,原因在于組織中的“人”并沒有被真正從內在調動起來。經理人都很期待員工或團隊有使命感,但經理人得首先闡明使命是什么,這就要求經理人要善于從工作的背后進行挖掘,賦予工作或任務以更崇高的意義。
壽險業行銷巨子、美國人柏特•派羅對他從事的壽險銷售是這樣理解的:“我們銷售的是明天不是今天,是未來不是現在。我們銷售的是安全、內心的安詳、一家之主的尊嚴以及免于恐懼、免于饑渴的自由,是天倫之樂與自尊,是希望、夢想和祈禱!”派羅為那些辛苦奔波、不斷遭受拒絕的保險代理人們指出了他們工作的意義。吉姆•柯林斯在他的著作《基業長青》中提到:“每個偉大的企業都有一個超越賺錢的目的。迪斯尼是讓人們快樂,惠普是做出技術貢獻……”這個“超越賺錢的目的”就是“組織的使命”,要培養團隊成員對組織的使命感,就要從發現工作的意義入手。
組織可以讓大家團結起來,組織的使命可以“讓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團隊或員工個人因看到工作的意義而感覺到一種責任,因肩負了這種責任而變得更加努力,這種動力是來自于內在的,是對神圣使命的追求,而不只是為了獎勵、提成,或者只是因為害怕沒有好好工作受到處罰而被迫行動,這種“被迫地積極”是不可能持久的。
工作的意義或使命感一經建立,會對組織中認同這一意義的成員們產生深刻影響,包括行動本身以及隨之而來的結果,它甚至會改變一個人的人生方向。影片中希爾茲上尉的變化就印證了這一點。希爾茲上尉是個摩托車賽車手,他很聰明也很執著,但他只想用自己的方法逃出去。在他聽到羅杰的那個有震撼力的計劃時,他認為“這太瘋狂了”,會導致整個德國都投入到搜捕當中來,根本不利于戰俘們逃出德國。當他理解到這正是計劃的真正意義(制造混亂,牽制德軍)后,他承擔起了最困難的任務,先逃出去,為大家探明營地外的地形和路線,然后再冒著被處死的危險主動“被抓回來”,帶回他的情報。這就是意義與使命的力量,它激勵著人們拋棄了個人安危,投入到組織的目標之中,它完全改變了一個人的想法、做法,甚至人生目標。
在羅杰少校所建立的使命感的推動下,戰俘營中盟軍的官兵們開始實施他們一系列的戰斗計劃,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澳大利亞人空前團結,聯合協作,經歷種種困難和危險,最終從戰俘營中逃出去70余人,雖然其中有50人在隨后的追捕中落入蓋世太保之手并被槍殺,羅杰本人也在這50人當中,另有近20來人被抓回并重新投入了戰俘營,最終成功逃脫、得償自由的僅僅幾人而已,但這次戰斗的目的——牽制德軍——其實已經達成。
有經驗的田徑教練會告訴你:“跳遠的時候,眼睛要看著遠處,你才會跳得夠遠。”經理人有責任培養自己發現的目光,讓自己和下屬員工看得更遠,發現工作的意義和組織的使命,為員工與團隊采取自主行動提供明確的方向、輸入內在的動力。
(作者:畢波 刊載于《21世紀商業評論》2008年10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