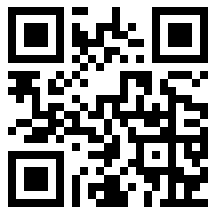文 / 施 煒,華夏基石管理咨詢集團(tuán)領(lǐng)銜專家、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中國(guó)資本市場(chǎng)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來(lái)源:中歐商業(yè)評(píng)論
核心觀點(diǎn):
1.企業(yè)需要持續(xù)進(jìn)化以在持續(xù)變化的環(huán)境中生存下來(lái),同時(shí)進(jìn)化是一個(gè)長(zhǎng)期反復(fù)的過(guò)程;
2.進(jìn)化不一定要顛覆式創(chuàng)新,關(guān)鍵是要?jiǎng)悠饋?lái);
3.顧客增量和迭代是企業(yè)業(yè)務(wù)進(jìn)化的基本方式;
4.絕大多數(shù)企業(yè)都不可能做生態(tài),但可以做團(tuán)簇式業(yè)務(wù)結(jié)構(gòu);
5.企業(yè)進(jìn)化最根本的牽引和制約因素就是價(jià)值觀及組織文化。領(lǐng)導(dǎo)者是企業(yè)進(jìn)化的關(guān)鍵變量。
“幸福的企業(yè)都是相似的,戰(zhàn)略清晰,組織能力強(qiáng);不幸的企業(yè)各有各的不幸。”
——施煒
在大家普遍關(guān)注騰訊、阿里等超級(jí)生態(tài)型企業(yè)的時(shí)候,絕大多數(shù)處于長(zhǎng)尾的、“被生態(tài)”企業(yè)們,各有各的活法。它們?cè)谧约旱念I(lǐng)域內(nèi)或成長(zhǎng)、或收縮、或停滯,基于自身文化和能力基礎(chǔ),企業(yè)家們?cè)谧龈髯缘倪x擇。
這些“被生態(tài)”的企業(yè),很多是中國(guó)第一批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企業(yè),它們已經(jīng)完成了原始積累,選定了企業(yè)的賽道,但在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新生代崛起、技術(shù)變革等場(chǎng)景下,它們面臨新的選擇。
對(duì)于那些選擇了不斷前進(jìn),乃至希望基業(yè)長(zhǎng)青、成為“百年老店”的企業(yè),它們應(yīng)該選擇什么樣的成長(zhǎng)路徑?如何變革自身走向百年?組織應(yīng)該作出哪些變革?管理學(xué)博士施煒在他的新書《企業(yè)進(jìn)化:長(zhǎng)期戰(zhàn)略地圖 》中提出了企業(yè)進(jìn)化算法和企業(yè)長(zhǎng)期戰(zhàn)略地圖。近期,《中歐商業(yè)評(píng)論》對(duì)他進(jìn)行專訪,就這幾個(gè)話題進(jìn)行了探討。
01、無(wú)論起點(diǎn)高低,企業(yè)進(jìn)化關(guān)鍵要“動(dòng)”起來(lái)
中歐商業(yè)評(píng)論(以下簡(jiǎn)稱CBR):中國(guó)企業(yè)為什么需要一套進(jìn)化算法?進(jìn)化算法能給他們帶來(lái)什么樣的價(jià)值?
施煒:中國(guó)企業(yè)和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比較緊張。目前主要有四大環(huán)境變化。一是技術(shù)發(fā)展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產(chǎn)業(yè)革命。很多中國(guó)企業(yè)過(guò)去技術(shù)基礎(chǔ)相對(duì)較弱。這些企業(yè)最大的擔(dān)心在于它有可能搭不上高科技這趟車;或者搭上了,卻又被甩下來(lái)。
二是“逆全球化”帶來(lái)的全球供應(yīng)鏈變化。對(duì)中國(guó)企業(yè)沖擊比較大的是純粹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和高科技產(chǎn)業(yè)。中國(guó)人口紅利在減少,勞動(dòng)力成本上升,有些產(chǎn)業(yè)會(huì)轉(zhuǎn)移到印度、越南這些地方;高科技涉及到國(guó)與國(guó)之間的競(jìng)爭(zhēng),抑制與反抑制斗爭(zhēng)會(huì)越來(lái)越強(qiáng)。
但是中國(guó)還有一類產(chǎn)業(yè)比較安全,它們有一定技術(shù)含量,但不是是最尖端技術(shù),也不是勞動(dòng)密集型。這些產(chǎn)業(yè)雖然沒(méi)有特別高的科技含量,但需要工程師和管理。東南亞國(guó)家在這些領(lǐng)域沒(méi)有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美國(guó)也缺乏大量的工程師供給。所以,中間型產(chǎn)業(yè)如家電、家具、小型機(jī)電包括一些裝備行業(yè),情況都還不錯(cuò)。
三是中國(guó)經(jīng)濟(jì)正在從規(guī)模經(jīng)濟(jì)進(jìn)入到質(zhì)量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市場(chǎng)增量越來(lái)越少,存量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非常激烈,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家具、建材、家電市場(chǎng)的狀況。雙循環(huán)之下,廣東很多出口型家具轉(zhuǎn)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市場(chǎng)供給增加,競(jìng)爭(zhēng)進(jìn)一步加劇。
四是企業(yè)與顧客的連接機(jī)制發(fā)生了變化。年輕消費(fèi)者的需求理念和消費(fèi)理念與他們的父兄極不相同。多種場(chǎng)景相融合,渠道、傳媒碎片化,企業(yè)營(yíng)銷難度越來(lái)越大,很難高效率地獲取顧客流量。目前只有極少數(shù)企業(yè)適應(yīng)了這個(gè)變化。
產(chǎn)業(yè)和市場(chǎng)變化帶給企業(yè)家三大痛點(diǎn)。一是戰(zhàn)略之痛,就是未來(lái)的發(fā)展方向在哪里,成長(zhǎng)路徑怎么安排,戰(zhàn)略和企業(yè)能力之間如何匹配?這意味著企業(yè)需要從過(guò)去的機(jī)會(huì)型成長(zhǎng)向能力型成長(zhǎng)過(guò)渡,這是一個(gè)時(shí)代話題。
二是學(xué)習(xí)之痛。坦率地說(shuō),今天商學(xué)院里真正能給企業(yè)家提供有效方法的老師和課程非常稀少。學(xué)校外有一些江湖派,講一堆不好操作的時(shí)髦理念,甚至還有只講點(diǎn)子不講方法的。企業(yè)家找好的學(xué)習(xí)產(chǎn)品是相當(dāng)難的。
還有一類管理概念,本身沒(méi)有問(wèn)題,但可能只適合于極少數(shù)企業(yè),比如現(xiàn)在流行的生態(tài)戰(zhàn)略。在產(chǎn)業(yè)里能做生態(tài)的企業(yè)可能只有0.01%,余下的99.99%的企業(yè)是“被生態(tài)”企業(yè),它們?nèi)绾紊妫攀顷P(guān)鍵問(wèn)題。
三是心力之痛,就是心力不足,驅(qū)動(dòng)力不夠。過(guò)去很多民營(yíng)企業(yè)家,尤其是50后、60后、70后企業(yè)家,他們中大部分人都有很深刻的貧困和饑餓記憶,有很強(qiáng)的財(cái)富沖動(dòng),這是他們創(chuàng)業(yè)時(shí)的基本動(dòng)力。
當(dāng)財(cái)富問(wèn)題基本解決后,企業(yè)家需從財(cái)富驅(qū)動(dòng)轉(zhuǎn)向使命驅(qū)動(dòng)。但是,一則前路風(fēng)險(xiǎn)更大、投入更大、不確定性更高;二則不少企業(yè)家也是平常人,也喜歡輕松舒適的生活。因此企業(yè)家群體中,缺乏使命驅(qū)動(dòng)的人數(shù)比例也不算低。
思考、解析這些背景,我梳理并構(gòu)思了企業(yè)進(jìn)化算法(圖1)和長(zhǎng)期戰(zhàn)略地圖(圖2),試圖為這些企業(yè)提供一個(gè)全局視野和系統(tǒng)思維。這套算法和地圖適用于三大類企業(yè):已經(jīng)完成原始積累、超越創(chuàng)業(yè)期、找到自己主賽道的企業(yè);技術(shù)追趕型的企業(yè),它們有向能力型企業(yè)轉(zhuǎn)型的驅(qū)動(dòng)力;以及有長(zhǎng)期戰(zhàn)略意圖、有產(chǎn)業(yè)思維的企業(yè)。


CBR:“進(jìn)化”是針對(duì)生物、有機(jī)體的,而企業(yè)則是一個(gè)機(jī)構(gòu),為什么引入這個(gè)概念,對(duì)理解長(zhǎng)期戰(zhàn)略地圖有什么價(jià)值?
施煒:我認(rèn)為企業(yè)也是生命體。進(jìn)化視角的主要思想之一是重視種群和外部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適者生存。“適”就是適應(yīng)環(huán)境,而現(xiàn)在環(huán)境不確定,如何適應(yīng)環(huán)境是非常重要的戰(zhàn)略課題。
作為一個(gè)復(fù)雜的生命體,企業(yè)需要在適應(yīng)環(huán)境、與環(huán)境互動(dòng)的過(guò)程中不斷發(fā)展結(jié)構(gòu)、機(jī)能,改進(jìn)企業(yè)發(fā)展模式,延續(xù)企業(yè)組織的生命。進(jìn)化是需要干預(yù)的,即需要戰(zhàn)略調(diào)整、管理改進(jìn)。進(jìn)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從量變到質(zhì)變,再量變?cè)儋|(zhì)變,反反復(fù)復(fù)、起起伏伏的長(zhǎng)期過(guò)程(圖3)。

進(jìn)化開始時(shí)起點(diǎn)高低不是問(wèn)題,關(guān)鍵是要?jiǎng)悠饋?lái),走上進(jìn)化之旅。中國(guó)企業(yè),尤其是很多民營(yíng)企業(yè)起點(diǎn)低、基礎(chǔ)差、沒(méi)有技術(shù)含量、附加值低。但是這些企業(yè)一旦走上迭代之路,實(shí)際上就開始進(jìn)化和成長(zhǎng)了。
需要說(shuō)明的是,成長(zhǎng)、迭代、進(jìn)化,不一定是顛覆性創(chuàng)新,99%的企業(yè)進(jìn)化都不是從顛覆性創(chuàng)新開始的。對(duì)于大多數(shù)企業(yè)來(lái)說(shuō),顛覆性創(chuàng)新遙不可及,就像智人不是一天進(jìn)化為人的。
02
數(shù)字化不是企業(yè)進(jìn)化的決定性變量
CBR:企業(yè)進(jìn)化模型應(yīng)該包括哪些變量?既然是算法模型,那么該如何開始呢?
施煒:企業(yè)進(jìn)化算法包括顧客價(jià)值進(jìn)化、生存及發(fā)展模式進(jìn)化和組織機(jī)能進(jìn)化這三個(gè)層次;包含增量、迭代、戰(zhàn)法、資源密度、能力和活力六大變量,以資源密度(主要指勞動(dòng)密度)為樞紐,貫通戰(zhàn)略和組織兩個(gè)層面。
一個(gè)企業(yè)選擇業(yè)務(wù)領(lǐng)域、確定商業(yè)模式之后,它的進(jìn)化從哪里開始?我的回答是顧客價(jià)值增量。增量就是變化,既包括新一代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差異化創(chuàng)新,也包括顧客代價(jià)降低的部分。
有時(shí)候顧客價(jià)值一小步意味著技術(shù)創(chuàng)新一大步。舉個(gè)工業(yè)品的例子,臺(tái)積電的晶圓制程從7納米進(jìn)步至5納米,馬上要做3納米、2納米,每一次看似微小的變化,都會(huì)引發(fā)設(shè)備、工藝的重大創(chuàng)新。
顧客價(jià)值增量源于顧客需求變化,抓住這個(gè)變量就基本處理好了與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
顧客價(jià)值增量的實(shí)現(xiàn)意味著顧客價(jià)值迭代。迭代很困難,以華為手機(jī)為例,頭幾年進(jìn)展并不順利。小米手機(jī)崛起對(duì)華為有很大沖擊,小米把華為的血性激發(fā)出來(lái)了。華為手機(jī)終于進(jìn)入進(jìn)化軌道,例如Mate10,Mate20、Mate30,Mate40……一代比一代好。這就是迭代。增量和迭代是企業(yè)業(yè)務(wù)進(jìn)化的基本方式。
CBR:中國(guó)企業(yè)從機(jī)會(huì)型成長(zhǎng)轉(zhuǎn)向能力型成長(zhǎng)時(shí),哪些能力最為關(guān)鍵?
施煒:說(shuō)到企業(yè)能力,我提出了一個(gè)與之相關(guān)的新概念,叫做資源密度,它是整個(gè)算法的樞紐概念。資源密度包括資金、技術(shù)、數(shù)據(jù)、人力資源密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資源密度,就是單位產(chǎn)品中勞動(dòng)的投入量,也叫勞動(dòng)密度。
勞動(dòng)密度取決于勞動(dòng)人數(shù)、勞動(dòng)時(shí)間、勞動(dòng)形態(tài)、勞動(dòng)強(qiáng)度等。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技術(shù)追趕型企業(yè)的勞動(dòng)密度主要與勞動(dòng)強(qiáng)度有關(guān)。而勞動(dòng)強(qiáng)度可分解為認(rèn)知密度和行為密度。
認(rèn)知密度就是思考問(wèn)題的深度和精準(zhǔn)、細(xì)致程度。想得深細(xì)透,所有事情的認(rèn)知密度都超越別人,企業(yè)肯定成功,所以企業(yè)的進(jìn)化要落實(shí)到認(rèn)知層面。行為密度是行動(dòng)的力度、動(dòng)作的頻次,意味著執(zhí)行到位。提高組織認(rèn)知密度和行動(dòng)密度主要靠人力資源開發(fā)和有效的組織學(xué)習(xí)。它們是提升組織能力的主要途徑。
組織機(jī)能里包括組織能力和組織活力。能力+活力=生命力,即動(dòng)態(tài)競(jìng)爭(zhēng)力。能力是企業(yè)本身具有的素質(zhì)。比方說(shuō),拉美排球運(yùn)動(dòng)員跳得高,扣球很厲害,能力特別好。活力是能力和資源被激發(fā)出來(lái)的狀態(tài)。中國(guó)女排好幾次獲勝,尤其陳忠和時(shí)代兩次得冠軍,主要靠隊(duì)伍的活力。能力沒(méi)法彌補(bǔ),但活力可以調(diào)整。活力是企業(yè)內(nèi)在的力量,組織架構(gòu)、運(yùn)行流程、企業(yè)文化都與活力相關(guān)。
中國(guó)企業(yè)大都屬于技術(shù)缺乏型,我們的優(yōu)勢(shì)是人口紅利、工程師紅利,所以我們用勞動(dòng)密度,尤其是高級(jí)勞動(dòng)、知識(shí)性勞動(dòng)的密度,來(lái)解釋中國(guó)企業(yè)未來(lái)成長(zhǎng)的要素和發(fā)展奧秘。
CBR:近兩年企業(yè)界比較高頻提到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您認(rèn)為數(shù)字化應(yīng)該在進(jìn)化算法的哪個(gè)環(huán)節(jié),屬于哪個(gè)變量呢?
施煒:數(shù)字化是企業(yè)成長(zhǎng)進(jìn)化的一種手段。數(shù)字化是當(dāng)今時(shí)代企業(yè)進(jìn)化的重要內(nèi)容和形態(tài),在顧客價(jià)值、經(jīng)營(yíng)方式和組織機(jī)能三個(gè)層面都有體現(xiàn)。數(shù)字化非常重要,但還不是企業(yè)進(jìn)化的決定性變量。
有些企業(yè)家在激發(fā)人方面往往缺少一些方法和耐心,所以總感覺(jué)人不行,總希望有一種技術(shù)能包治百病,在數(shù)字化方面也有這種傾向。但是,沒(méi)有認(rèn)知密度、行為密度,數(shù)據(jù)有什么用?某些電信巨頭有海量大數(shù)據(jù),但進(jìn)化最快的行業(yè)和企業(yè)里都沒(méi)有它們。所以,數(shù)據(jù)重要,但不能迷信數(shù)據(jù)。
CBR:整體來(lái)看,企業(yè)進(jìn)化算法更適合傳統(tǒng)企業(yè),對(duì)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適用么?
施煒: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現(xiàn)在多數(shù)還處于資本助力階段,有強(qiáng)大的資本紅利或資本市場(chǎng)估值紅利。從長(zhǎng)期角度看,它們需要進(jìn)一步構(gòu)建顧客價(jià)值優(yōu)勢(shì)。比方說(shuō)拼多多的顧客價(jià)值是便宜,但便宜是因?yàn)橛芯揞~補(bǔ)貼。資本紅利耗盡之時(shí),它能否構(gòu)建起有競(jìng)爭(zhēng)力的供應(yīng)鏈,能否持續(xù)以較低的價(jià)格滿足顧客需求,那就要靠它的組織能力和活力了。
總體而言,這個(gè)模型更適合傳統(tǒng)的實(shí)體經(jīng)濟(jì),而不直接針對(duì)虛擬經(jīng)濟(jì)。

03
核心人才的邊界就是企業(yè)發(fā)展的邊界
CBR:現(xiàn)在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中的企業(yè),屬于您定義的傳統(tǒng)企業(yè),還是虛擬經(jīng)濟(jì)的一部分?
施煒:在可預(yù)見的時(shí)間里,大部分企業(yè)不可能變?yōu)樘摂M經(jīng)濟(jì)。阿里、騰訊都是超級(jí)大的平臺(tái)型企業(yè),但平臺(tái)本身不是沒(méi)有邊界的,也不可能把所有企業(yè)形態(tài)都納入到平臺(tái)之中。這就意味著,大部分企業(yè)實(shí)際上還是處于產(chǎn)業(yè)生態(tài)背景下相對(duì)獨(dú)立的生存發(fā)展?fàn)顟B(tài)。
但是,不是所有做不了生態(tài)、成不了平臺(tái)的企業(yè)就要被生態(tài)、被平臺(tái),企業(yè)可以形成自己的小生態(tài),橫向以顧客資源、技術(shù)為基礎(chǔ),長(zhǎng)出幾塊業(yè)務(wù);縱向以產(chǎn)業(yè)上下游為基礎(chǔ),也可以長(zhǎng)出幾塊業(yè)務(wù)。這樣就能形成縱橫交錯(cuò)、相對(duì)關(guān)聯(lián)的團(tuán)簇式的業(yè)務(wù)結(jié)構(gòu)。我把這種業(yè)務(wù)拓展模式概括為生態(tài)化擴(kuò)張。
比如深圳的立訊精密,連接器、光學(xué)模組、聲學(xué)模組都是縱向一體化的業(yè)務(wù),同時(shí)將它們從電腦延伸至手機(jī)、可穿戴設(shè)備、汽車等領(lǐng)域。很多產(chǎn)品都是以顧客資源和精密制造為基礎(chǔ),繁衍發(fā)展起來(lái)的。
CBR:團(tuán)簇式發(fā)展是個(gè)有趣的概念,但團(tuán)簇式發(fā)展的邊界在哪里?哪些企業(yè)該自己做,哪些該和產(chǎn)業(yè)鏈上下游合作?包括華為芯片被“卡脖子”的事件,真正前沿的技術(shù),是否必須自己投資?
施煒:華為是個(gè)例,不具有代表性。正常國(guó)際秩序下,電子及芯片產(chǎn)業(yè)企業(yè)之間是要進(jìn)行水平分工的。上下游那么多環(huán)節(jié),企業(yè)不可能全部都自己做。而且芯片本身是個(gè)超級(jí)大產(chǎn)業(yè),垂直整合往往超出了企業(yè)的能力范圍。
團(tuán)簇式生長(zhǎng)的限制,主要來(lái)自于核心人才。所謂核心人才主要指能獨(dú)當(dāng)一面的經(jīng)營(yíng)領(lǐng)軍人才。發(fā)達(dá)國(guó)家人才比較社會(huì)化。例如,亞馬遜需要的核心人才,在社會(huì)上有可能找得到。但在中國(guó),這類人才很稀缺,遇到、找到以及內(nèi)部培養(yǎng)都很有難度。并不是所有企業(yè)都能發(fā)現(xiàn)和培育核心人才,而這些人是企業(yè)發(fā)展的邊界所在。
比如小米采用了與外部成熟企業(yè)家合作的生態(tài)化擴(kuò)張模式。小米團(tuán)簇式發(fā)展有一個(gè)重要條件,就是主業(yè)足夠突出,手機(jī)市場(chǎng)表現(xiàn)好,小米的品牌就有價(jià)值,其他企業(yè)家或創(chuàng)業(yè)者就有意愿加入小米生態(tài)。此外,雷軍本身有影響力,企業(yè)內(nèi)部有強(qiáng)大的賦能能力。
CBR:企業(yè)領(lǐng)導(dǎo)者在企業(yè)進(jìn)化算法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
施煒:領(lǐng)導(dǎo)者是企業(yè)進(jìn)化的關(guān)鍵變量。我提出進(jìn)化型領(lǐng)導(dǎo)的概念。進(jìn)化型領(lǐng)導(dǎo)一是要有使命和追求;二是要有長(zhǎng)期目標(biāo)和戰(zhàn)略;三是要有實(shí)踐智慧,也就是把事情做成的能力——進(jìn)化中會(huì)遇到很多困難,要帶領(lǐng)團(tuán)隊(duì)打勝仗;四是要有平常人格;不是平常人就不能理解平常人的喜怒哀樂(lè),與團(tuán)隊(duì)就會(huì)有隔閡,就不可能形成高度融合的團(tuán)隊(duì)。
很多企業(yè)家具有英雄人格,老做英雄狀,那企業(yè)離出事就不遠(yuǎn)了。我們看到很多著名企業(yè)領(lǐng)導(dǎo)人,都是很普通的人,但長(zhǎng)期堅(jiān)持上面所說(shuō)的“四有”,做出了不平凡的業(yè)績(jī)。